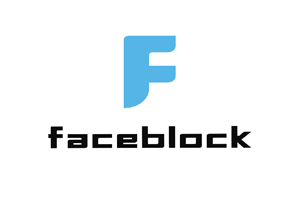透过智能技术、特别生物学、人类学的演进,可以明显感受到目的论思想的复兴。主要有两个:一个是重新思考人类携技术共同进化的方向,另一个是从这一方向的崇高性来论证技术介入生命的合理性。也就是说,出于西方数千年来强烈的宗教情感,即便创造一个无人格化上帝的“新宗教”,也不失为“拯救”的新途径。
从这个意义说,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圣哲,从未远离西方文化生活的左右。它是活生生的。但对于东方而言,却是冷冰冰的。
3) 20世纪七十年代心灵哲学的兴起特别有代表性,值得深入思考。上帝死亡、诸神离场之后的世界是难以忍受的。对上世纪上半叶旷世灾难的反思,从阿伦特“平庸的恶”、纳斯鲍姆《善的脆弱性》来看,西方思想家的视野,始终没有远离对人性的追问,但这一追问显然在酝酿着更加深刻的思想。我理解这一思想,就是再次以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悲悯情怀,重新看待善恶的关系。善恶关系在古希腊、希伯来文化合流的那段时间,从耶稣受难到圣奥古斯丁的350年前,经历了数百年的血腥冲突,从人性与神性、上帝恩典、位格之争,到邪恶的本质、创世与堕落、受生与受造,最终确立三位一体、道成肉身的正统一神论、一元论内核。上世纪50年代开启的反叛思潮,只是点燃了重新思考基督世界两千年文明史的序幕。非常遗憾的是,过去的半个多世纪,中国人再次与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苦旅无缘。
东西方文明交融和交流的历史阡陌,极其孱弱,极其泥泞。如果这一波思想动荡的历史进程中,双方再次无法聆听对方,再次无法深度体察激荡于心的内心洪流,反而受缚于表面的词语藩篱,历史的错失将不可避免以悲剧形式发生
从这个意义说,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圣哲,从未远离西方文化生活的左右。它是活生生的。但对于东方而言,却是冷冰冰的。
3) 20世纪七十年代心灵哲学的兴起特别有代表性,值得深入思考。上帝死亡、诸神离场之后的世界是难以忍受的。对上世纪上半叶旷世灾难的反思,从阿伦特“平庸的恶”、纳斯鲍姆《善的脆弱性》来看,西方思想家的视野,始终没有远离对人性的追问,但这一追问显然在酝酿着更加深刻的思想。我理解这一思想,就是再次以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悲悯情怀,重新看待善恶的关系。善恶关系在古希腊、希伯来文化合流的那段时间,从耶稣受难到圣奥古斯丁的350年前,经历了数百年的血腥冲突,从人性与神性、上帝恩典、位格之争,到邪恶的本质、创世与堕落、受生与受造,最终确立三位一体、道成肉身的正统一神论、一元论内核。上世纪50年代开启的反叛思潮,只是点燃了重新思考基督世界两千年文明史的序幕。非常遗憾的是,过去的半个多世纪,中国人再次与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苦旅无缘。
东西方文明交融和交流的历史阡陌,极其孱弱,极其泥泞。如果这一波思想动荡的历史进程中,双方再次无法聆听对方,再次无法深度体察激荡于心的内心洪流,反而受缚于表面的词语藩篱,历史的错失将不可避免以悲剧形式发生
0
0 评论
0 股票